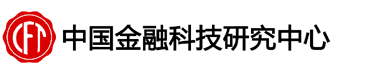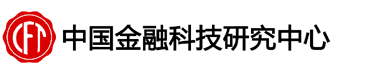柔性监管是一种与命令控制色彩浓厚的传统监管相对应的新型监管,有着权力中心多元、重协调与互动、重过程等基本特点。从监管方式上看,其十分注重监管的灵活性、柔软性(非强制性)。
主要通过协商、激励、指导、自我监管数据监测、信息披露、窗口指导、约谈等软性方式的运用来提高监管的实效。事实上,我国在互联网金融时期的监管便很好地体现了柔性监管的思路,其与监管沙盒有着十分相近的治理逻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互联网金融“先发展后规范”监管思路的践行,以及“鼓励创新与加强监管”并重方针的强调。2013年被称为我国的互联网金融元年,以此为界点,互联网金融各业态开始野蛮增长。数据显示,中国大陆2013年至2014年的网纟各替代金融成交量从55.6亿美元增长到了243亿美元,年增长率为337%;2014年到2015年,报告成交量继续增长了319%,达到了1016.9亿美元。
但监管部门并未第一时间就出台规则来对其进行管控,直到2015年7月和2016年4月,才陆续发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和《互联网金融风险整治方案》对其进行规制。在具体的路径上,则明确指出要“通过鼓励创新和加强监管相互支撑,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遵循“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创新监管”的原则和“鼓励创新、防范风险、趋利避害、健康发展”的总体要求来进行监管。无疑,此种体现柔性监管思维的“先发展后规范”的思路、提供试错机会的模式,以及鼓励创新与加强监管并重的要求,与金融监管沙盒制度在限定范围内进行试错,以平衡创新与风险的方式十分相近,为其在我国的构建与发展提供了监管思路上的温床。
二是协商性监管平台的搭建。监管部门与创新主体之间的命令一一控制型监管促成了两者的对立,不利于金融科技的良性发展。此时,一种排除自上而下的阶层关系,充分尊重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注重监管的合作与交流的互动型监管关系便成为更优的选择。这同样也是监管沙盒平等博弈和充分交流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在这方而已经有所实践。典型如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组建的互联网金融协会,旨在对互联网金融行业进行自律管理,同时承担若协调会员之间、协会及其会员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簪任务,其成立以来发布的各类自律规则和相关报告,均是监管部门和行业土体共同参与的结果。
如前文所言,随着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大数据、分布式账本、云计算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在金融行业的混业经营已成定局的趋势下,更加模糊了各金融子行业的界限,使得传统金融风险和科技风险叠加,并更具时间和空间的传染性。这无疑对我国当前的分业监管体制和不完善的监管协调机制提出了重大挑战,监管真空、监管重叠、监管俘获和监管套利等问题日益凸显,再度激化了混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制度性错配矛盾。长期以来,我国都在为缓解这一矛盾进行努力。
例如,国务院于2013年8月批复同意组建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中国证监会、中国银监会、中国保监会和外汇局共同参与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该会议在必要时可以邀请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参加;2015年7月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各监管部门要在分类监管的基础上相互协作,充分发挥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的作用,并实现统计数据和监管信息其享;
2017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应当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高级别的、有实体机构的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来统筹金融发展和监管协调的问题,该委员会于2017年11月正式成立,其职责包括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统筹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相关事项,统筹协调金融监管重大事项,协调金融政策与相关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等;
无疑,我国近年来的此类监管体制改革,一方面契合了当前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监管沙盒内含的监管部门间互动型关系的要求。例如,英国在其《监管沙盒》文件中就指出,当受到双重规制的创新公司进行测试时,FCA将会同审慎监管局共同协商来选择具体的沙盒制度;
我国台湾地区规定主管机关在审查创新试验及其结果时,应当召开有相关专家和机构(机关)参与的审查会议;我国香港的金融管理局在其前期运行监管沙盒的经验基础上,与香港证监会、香港保监局实现了监管沙盒的相互协调运作,为跨界金融科技项目提供了“一点通”的接入服务,等等。以上种种,显然为金融监管沙盒制度在我国的落地提供了体制上的生长土壤。
我国自由贸易园区概念体系下的保税区、经济特区、岀口加工区、保税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特殊区域,以及在特定的地域、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所进行的局部性政策探索测试之“试点”模式。与金融监管沙盒有着类似的“特定性”或“试验性(探索性)”之内在逻辑,其模式都是在特定的范围内实施特殊的监管措施,内蕴着缓解新的现实与既定法律之间矛盾的思维进路。
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例,自2013年上海自贸区成立以来,我国以“暂停相关法律实施”为基础的自贸区,己经形成由点到线再到面的格局,成为先行先试的典范。虽然一些学者对国务院是否有权设立自贸区、是否有权暂停法律实施以及自贸区的行政地位等问题颇有微词,但实际上《宪法》第62、67和89条已经为其提供了答案。同时,突破既有模式或规则或做法,显然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所谓的试验,也不是恣意妄为,而是在遵循合法规则的前提下的大胆创新。
且就目前各大自贸区制定的相关规则而言,也并无逾越立法等级之樊篱的情况出现。从本质上看,金融监管沙盒制度与我国的自贸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前者是由监管部门运用其豁免权来放宽法律对创新主体的适用,从而在限定的范围内进行测试;后者则是通过对现有规则的变通执行,实现在特定区域内的先行先试。两者共同遵循的原则都是不与现有法律框架冲突和在法律的授权范围之内。例如,英国、澳大利亚等均对其豁免方式所适用的产品、超出主管机关权限范围外的协调等内容进行了反复强调。